


何志平与一众可爱的北大学子,就国家发展机遇、个人事业前途展开了多场深入的交流。(作者供图)
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发展现状及人才培养
文/何志平 龚亮容
近年来,内地教育总体水平已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其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香港学生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有信心,希望把握新时代国家发展脉搏,谋划自身未来发展。
龚亮容(香港青年,20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2023年4月,香港教育局公布了“2022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当中接受调查的38610名学生中,12.4%选择离港升学,而前往内地升学占比最高,达39%。北京是港澳学生最常选择升读的地方之一。

龚亮容。(作者供图)
香港学生在内地升学有其优势。首先,香港学生在港普遍接受过两文三语及品德培育的训练,有不同的特长与学科兴趣,在不同院系和专业都能发现香港人的身影,不同的社团组织也有活跃的表现。其次,港澳教育制度能为所有学生提供优质而平等的机会。第三,香港不少中学除重视学生的学业表现,更重视学生的均衡发展,包括社交能力、兴趣培养、领导能力等等。学生透过参加不同的课外活动,领导能力逐步提升,可推动社区发展和文化交流。第四,香港自回归后实行“两文三语”的语文政策,即中文、英文书写,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口语,这种多语能力有助促进跨文化交流,掌握国际机遇。
而重中之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学生普遍视个人拥有世界视野为重要之事,因此在中学毕业后都会前往外地升学。他们希望冲出香港,扩阔视野,增加不同发展的可能性、增强自身竞争力。选择来到内地升学的同学,除以上想法之外,还希望提升对国情的了解。然而北京高校的港澳学生也有较弱的地方:
首先,香港学生相对内地学生,数学水平普遍欠佳。由于香港中学所授数学,都比内地中学难度低很多,内地港生的数学水平不足以应付课程需要,普遍面临着高等数学不及格的问题。
另外,港澳学生在北京生活四年或更长时间,未必了解港澳讯息万变的情况。若要回到本地发展,必然需花更多精力熟悉港澳社会文化和职业市场环境,重建人脉,相较本地升学的港澳学生,较难有深入的了解。
再者,内地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法律体系存在差异,若回港可能需重新学习香港的法律法规。例如,一些内地毕业的香港学生若希望成为一名律师,一般会在香港高校再报读硕士进修,而香港升学的法学同学则不用再花时间。
何志平:
亮容反映的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发展现状,也是目前众多香港青年在国外留学念书的必然经历。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种族肤色不同,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我也有着十六年的异国他乡求学放洋的日子,所有人都在追梦,为了成才,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港澳学生到内地高校求学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大家刚刚讨论所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寻差,寻求两地培养人才的差距,寻找一些在香港无法找到的东西,扩认知,拓视野。内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河川秀美,各地多民族风土人情各异,高科技制造业发展迅猛,火箭太空舱遍天,内地学生从小就知上下五千年和大国之大也,这是“大国视野”;香港人口密度是北京的80倍,却寸土寸金、活力繁华,东西文化汇聚交融,国际化程度极高,孩子们一张口就是两文三语,有的是“国际视野”。港澳学生赶赴内地读书,除了念好专业专科技术,最重要的是培养何谓“国之大者”,要立大志、明大德,努力成大才、担大任。而内地孩子报考香港和国外大学,主要是为了学习接触国外先进的学术水平,开拓知识面和国际化思路、视野。要知道,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人的格局,而格局决定结局。格局大则世界就在脚下,格局小眼下就是整个世界!
想当年,晚清西方列强的侵略举世皆知,国家要想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变法兴国,更好地了解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与工业技术,于是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这些人走出国门,带回来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技能,为近代社会进步和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鼓舞了后来更多的年轻人出外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现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状态下,人才成为引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我们需要用新的理念来思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从新的角度去解读和应对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读好了书,或学会钻研掌握了一门技术,你就可能成为一个精通某一方面的专才。可那是“术”,还不是“学”。“学”是懂得怎么做人,做有智慧、有思想见地的通才、全才、领袖。而领袖则是在特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不是我们去找回来的。人才也不是靠培养,而是自我有机地成长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充分创造人才成长的土壤,提供养料、环境和生长成才的必需元素,从而让人才种子发芽茁壮、结树成荫。而作为种子的学子,则需主动寻找一块适合自我成长的沃土。既乐在其中,又能成才,扶摇直上,睥睨脚下一片天!
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大湾区,甚至香港,澳门,真正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既极具“国际视野”,又胸怀“国之大者”的新青年!他们自会在新时代的新天地之下,追逐创造他们的“中国梦”、“香港梦”。香港青年,你们准备好了吗?
没有英女王像 也没有升旗仪式的皇后像广场
文/何志平 孔翔乐
孔祥乐(香港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自其诞生伊始,便会携带着独特的胎记:独一无二的历史和精神风貌。每个地方总有一些地标、抑或是一些建筑,例如一片充满当地特色的中央广场,能让居民和游人一同穿梭其中,感悟此城此地的历史与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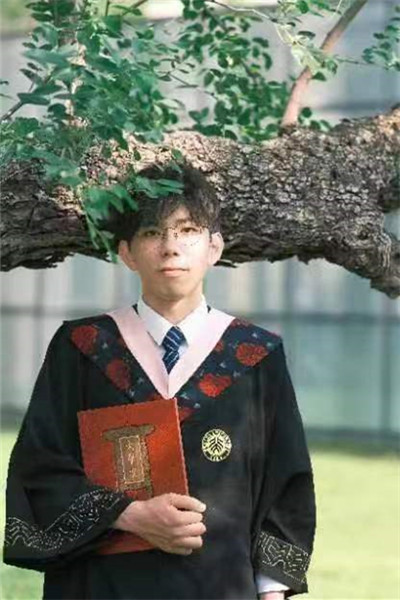
孔祥乐。(作者供图)
香港的皇后像广场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广场肇建于十九世纪末,起初安放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等九尊铜像,因而得名(误译)为皇后(Queen)像广场。二战前,女王铜像与第一代皇后码头共同构成了广场的中轴线,并与四周(从十二点方向顺时针数起)的汇丰银行大厦、太子行(商业大厦)、皇后行(商业大厦)、皇后码头、和平纪念碑、香港会所大厦、最高法院和旧香港大会堂(剧院)等建筑共同组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与其他地区的中央广场一样,这里有一片用以举行大型活动和庆典仪式的草坪,也有一座用以悼念英烈的纪念碑和有一尊用以瞻仰的雕像。这里同样有一座用以举办演出的剧院,有一幢雄伟壮观的政府建筑(出自伦敦白金汉宫设计师的手笔)。不同的是,这里少了一杆象征殖民地和属国的旗杆,多了许多商业大厦、银行和会所。由此可见,战前香港以女王铜像取代了属国旗帜的作用,殖民者们期望以这种软性手段凝聚香港岛上的商业社会。
日占时期,皇后像广场被蹂躏得面目全非。重建后横跨在中轴线上的第三代汇丰银行大厦被改作“香港占领地政府”总部,顶楼增挂日本国旗。拱顶亭座里的女王铜像则被掳到日本,换成《香港占领地总督告谕》石碑。旁边的最高法院被改作宪兵(行政和司法警察)总部。至于刻着一战年份的和平纪念碑,以及其他商业和文娱设施,固然无法为占领军二次利用。总的来说,广场上新增了旗杆、行政机关、军事警察机关、告谕,这一切建筑皆在直白地宣示其绝对的统治权威,与广场肇建之时的“软性宣教”的规划意趣截然不同。
何志平:
翔乐的皇后像广场感受,也是很多内地朋友第一次到埠香港的直观感觉。后来近年香港状况频出,专家学者们都认为,香港问题的关键是“去殖民化”的工作长期以来都没有做好。军事学者金一南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工作。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韩国的“去殖民化”,再看看蒋介石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我以为,香港“去殖民化”首先应从青年的去殖民教育开始。
150多年来,香港虽然政治上与中国母体离异,地理上却是紧贴她的边缘,有若干经济和文化交流,香港人的生活文化也是承袭中国文化;加上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定开始明朗化,这些都是港英殖民政府难以回避的事实。因此,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政策基本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本地的社会情况而有所变更,变更的分水岭在1966年。1966年前,从香港开埠以来,香港政府教育政策都以本把英国籍人士和“高等华人”为服务对象,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香港殖民政府培养本地公务员,和为英国商行培养本地华人精英的买办行政人员和秘书;至于本地青年服务工作,由于当时教育还未普及,主要由民间组织如西方教会和华人自发自组的善堂等担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殖民政府对大陆的新政权,以及其新确立的国民主义对香港民间的影响有所顾虑,大力打压本地爱国青年团体,强行解散由亲共产党人士设立的书院等,例如当时位于香港新界屯门的达德书院,便是受打压的明显对象。1949年以前,香港华人子弟还可以自由地到内地读书;但1949年后,罗湖边防被关了,香港居民不能自由地往返大陆家乡,众学生也只能在香港本地上学了。但那时候大中小学校的学位有限,学费也不是一般贫苦的劳工大众可以负担得起的,再加上50年至60年代期间,大量内地居民落地香港,本地人口剧增,流浪街头讨食的“街童”,和在居苑天台上课的“临时”课室或学校,亦都成为那时代的社会现象。及至1966年,因天星小轮加价事件酿成的骚乱以及1967年的反殖民政府暴动,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本地青年学生工人,当时殖民政府马上意识到忽略青年问题会带来严重管治危机,制定青年政策成为当时殖民政府的重要任务。70年代初,港英政府痛极思痛,在新港督麦理浩到任后推出种种的民生普惠政策,其中包括公帑资助九年免费的普及教育,从而开展了“人人有学上,教育知多少”的殖民地思想教育。
总的来说,英国对香港青年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心思想是抹杀香港青少年的中国人政治身份、中华儿女的文化身份、国家栋梁的未来主人翁身份和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领袖身份,分为以下四个方式:
一是去政治化,以消磨青年对殖民政权的不满情绪为目的,除了在1967年后举办新潮舞会、香港节和地区暑期活动,用文化休闲康乐活动转移政治焦点外,学校工作就是培育守规矩、安守本分的市民。
二是去中国化,在教育语言上重英轻中,标榜英语的优越性和社会高等地位,同时在中国历史课中大量删减介绍近代中国的内容,中国历史课只谈到鸦片战争。
三是妖魔化,渲染青少年犯罪、吸毒和黑社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目的是要使整体社会认同青年是社会的定时炸弹,把青年边缘化。
四是技术化,即加强职业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培养相关领域人才,另一方面以重视专业技术人士非政治化的身份,甚至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笼络青年加入政府,让青年成为殖民政府的拥护者。
难怪钱穆先生早在60年代便预言:“香港只有居民教育,而无国民教育;只有职业教育,而无人才教育;只有语言教育,而无文化教育。在这样的氛围下,只会培植出伶牙俐齿的专业人士,他们只懂追逐名利与个人成功,而缺乏文化理想、群体意识与国家观念。”
如今香港主权回归祖国26年了,“去殖民化”迫切需要提上政治议程!

香港新闻社
有视界·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