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志平與一中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作者供圖)
港生清華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感想
文 | 何志平 李震庭
李震庭(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北京石景山區青聯委員、全港各區工商聯青企副會長):在清華的三年多裏,有過疲憊、猶豫和迷茫,也有過興奮、欣慰和釋然。典雅莊重的清華園的學習生活,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你總是會有看不完的書,幹不完的活,想不完的事。學術、社會工作和生活之間的來回切換,總是會帶着一層又一層的壓力。我在學會釋懷這些壓力的同時,把書讀好,把事做好,是這幾年我感觸最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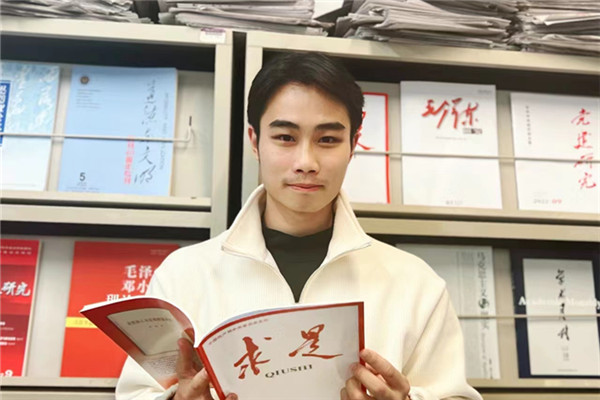
李震庭認為在清華的校園生活是一種挑戰。(作者供圖)
夯實基礎,才能學有餘力。在我看來,學則是一切發展的前提。我在碩士階段完善了自己的觀點、立場、方法,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有了充分掌握後,在博士階段才開始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在系統的閱讀了《資本論》三卷後,我決定以香港的經濟制度為基礎,以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香港的產業結構演進中的路徑、挑戰與出路。
主動作為,才有突破可能。清華匯聚了各方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對我們香港學生也很寶貴。學校會組織講座座談、實習實踐等活動啟迪我們思考,幫助我們探尋發展方向;也看重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育,給予資源和平台的支持;更會鼓勵香港青年學生結合自身優勢,探索自身發展不同方向。當然,這也需要我們抓住機會,敢於主動。我就在擔任香港研究生組組長期間,在學校的指導下,積極舉辦香港青年學子與有關政府部門領導的會面交流,組織學生深入祖國各地開展國情實踐,在幫助更多香港同學擴展視野的同時,也逐漸明晰自身的發展路徑。
持之以恒,才能進而有為。清華的校風一直是又「紅」又「專」,全面發展。而清華的香港學生,尤其是很多師兄師姐在愛國愛港、敢於擔當的文化熏陶下,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學習態度和嚴謹的工作作風,牢記愛國愛港之初心使命,在各個崗位上奮發有為,幹出了令人羨慕的成績。我也一直激勵自己認真學習,磨練本領。希望畢業之後回到香港,能到政府部門工作,充分發揮自己所長,助力建設美好香港。
何志平教授:清華,北大,都是中國最重要的高等學府。它們歷史悠久,都具有世界級學術水平,都在全球享有盛譽。尤其學成畢業的學生,幾乎都是行業天驕。震庭你們,有幸趕上新時代,得以其中學習,實乃人生一大快事!
我關注到去年教育部公布的自十八大以來,內地高校已累計招收港澳台學生7.9萬名,內地已連續多年成為港澳學生赴港澳以外地區升學的首選。同時,據早前一內地港生組織的「內地港生畢業回港意願調研報告」結果顯示,超半數51%受訪者從內地高校畢業後當年選擇回港工作,亦有46%受訪者表示目前選擇前往內地發展,比畢業當年選擇內地就業的比例22%增加了一倍。
如同震庭一般,這幾年有幾萬的內地港生畢業後返回香港,希望服務社會,或者從政加入政治機制行列,這絕對是好事。但有沒有人認真想過,如今的香港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治理及政治人才?或者換句話說,不管內地畢業的港生,還是外國畢業的港生,只要願意回港就業的你們,又有什麼樣非一般的本領或腦洞大開的新思路可引領影響香港文化教育、社會心態和政治民生回歸正軌?
當然,我之前說過,新時代下香港真正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既極具「國際視野」,又胸懷「國之大者」的新青年。雖然香港青年有一定的國際視野,然而在內地讀書多年的你們,是否發自內心地理解明白「國之大者」的重要內涵和時代價值?只有當一個人和國家命運共振的時候,族群的氣運也會集於一身,這就是高明之見和格局,就是「國之大者」。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會大胸懷、大氣魄、大擔當、大胸襟、大智慧、大格局和大作為,屆時無論「俠之大者」也好,文之大者也好,商之大者也好,我們一切的思想行為也必然會與「國之大者」相通。只有與「國之大者」相通,有了這種「為國為港為民」乃「國之大者」的站位,才是真正回歸和領悟通透。面對香港問題,方能與時俱進,以及東西並用!
我有時在想,如何讓在校的香港青年人在短暫的大學生涯中,從以單一學科為半徑的封閉小圈子裏跳出來,不斷與內地社會接軌,直接與內地社會對話?或者,剛剛走出校門的你們,尤其是準備從政加入政治機制行列的,可否考慮先在內地的政治體制內工作,哪怕只是在農村鄉鎮做群眾工作,累積二、三年鍛煉經驗後,再回港從政就職便能更駕輕就熟。甚至香港政府方面及相關社會組織機構,或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協商,一方面考慮城市之間的公務員相互借調,交流學習;另一方面像震庭這樣的有志青年們,初入社會,在通過相應的初級選拔考試後,先掛靠服務於內地城市的基層組織,體驗內地公權力機構的工作、發展,幾年之後再回流到香港政府部門。
可能這樣,才會在最短的時期內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言辭能同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對國家政策法規的理解非常正確、非常深入,執政策略、路線思路能站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最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且為香港眾多社會階層謀求「兩制之利」的香港特區政府新時代的公務員們。
如今香港人才引進如火似荼,搶人計劃轟轟烈烈,但我們為何不召喚並悉心凝聚內地畢業的港生呢。我們自己的,回流後首先就是新一代有廣泛見識的人才。不過,還是那句老話,來了香港,就是香港人!這當中,既包括新一代的本土年輕香港人,更包括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長大、現又在有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作和生活的新一代香港移民,大家互相融合、感染、影響,從而披荊斬棘,為香港另創一番新天地!
由「省港大罷工」後的「振興國粹」看今日香港
文 | 何志平 孔翔樂
1925年夏,為響應在上海爆發的五卅運動,大量香港工人經號召離港返粵,史稱「省港大罷工」。據統計,當時有超過25萬香港居民(當時全港總人口僅60餘萬)曾參與罷工、罷課和罷市,一度嚴重危及港英政府的殖民管治,可謂香港史上一樁大事。回望港英當局當年如何鎮壓安撫,我們便能發現港英政府除了修訂《非法罷工與停業條例》、啟用《緊急法》之外,還有一系列耐人尋味的「振興國粹」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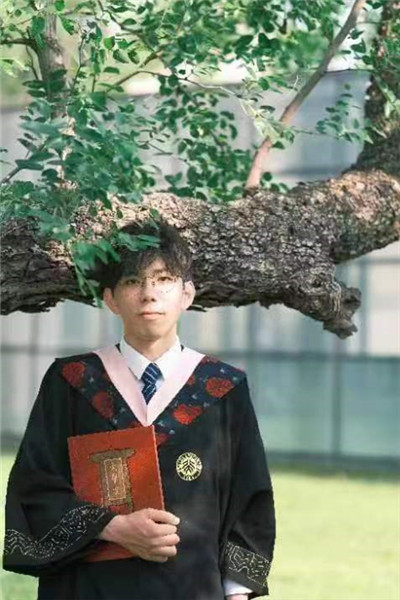
孔翔樂認為金文泰在香港推行「振興國粹」措施另有所圖。(作者供圖)
孔翔樂(香港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生):罷工爆發後,倫敦方面不滿時任港督司徒拔主張出兵北伐,於是臨陣換帥,提拔官學生(今政務主任的前身)金文泰為港督。金文泰畢業於牛津大學,早在八國聯軍侵華前便已赴港學習工作,深諳中國文化、國情和民情。他領導下的港英政府始終堅持「左派革命」定性,成功轉移「反帝國主義」矛盾,以拒共、疑共、恐共、抗共的「反共產主義」旗幟「團結」香港民眾和商界。
金文泰是「振興國粹」這一措施的「始作俑者」。1927年6月28日,《循環日報》全文刊登了他在香港大學倡議成立香港大學「華文學系」的粵語演講。他鼓動提高中文學業,並稱「第一系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第二系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第三就系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呼籲香港各界對於「香港大學文科、華文系」贊襄盡力,務底於成,同時「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翌日,金文泰又邀請了曾拒絕在中華民國任職的滿清遺老賴濟熙太史,以及香港華人領袖周壽臣爵士,在督憲府舉行茶會討論如何「振興國粹」。賴濟熙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周壽臣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乎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金文泰則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云云。
難道,這位英國紳士遠赴重洋「振興(中國)國粹」,是為了打造「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使「中英感情更融洽」嗎?當我們仔細咀嚼他的演講,便能體會不一樣的意圖。他引用的那句「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出自東漢班固《封燕然山銘》,原是竇憲將軍大敗匈奴後紀念軍功的摩崖文字,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意。只不過,他口中的「韃虜」不可能是滿清,更不可能是英國人自己,只能是當時新文化思潮或革命的共產黨。
「國粹」的內容本身包羅萬象,但金文泰要振興的「國粹」卻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他重用的知識分子是痛恨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禮崩樂壞」的滿清遺老,看中的「國粹」是「中國舊道德」。翻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經學講義》等教材,大家就會發現該「國粹」絕不是「彼可取而代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等中華文化裏固有的「敏感話題」,而是封建禮教、忠君愛國等為古代帝王提供統治秩序的保守價值。千百年後,港英政府重新挖掘這些有助維持社會穩定的思想資源,在香港塑造保守的政治文化、道德和思想,與北方的「五四」精神、革命理念分庭抗禮。
正當「中國舊道德」以鬧劇般的形式在香港進行回潮,內地卻在如火如荼地「鬧革命」。已建立四年的中國共產黨在「省港大罷工」後,黨員人數從1925年9月的3000人激增至1926年12月的18500人。後世學者稱,「1920年代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革命由此被建構為高於一切的普遍觀念和救亡圖存的根本手段。」而我們的香港,則在數十年裏「告別革命」,再無大規模罷工乃至社會運動。
何志平教授:感謝翔樂,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希望大家可以反思對比自金文泰在香港推行「振興國粹」措施後,香港社會一系列耐人尋味的變化!
從某種程度上說,金文泰的上任代表着香港的一次轉折,首先結束了香港此前長達40年的黑暗時期。且繼他之後的三任港督皆採用休養穩定政策,香港經濟開始快速發展。但同時,金文泰又堪稱香港與內地區隔的創始人。因為,他的「復古」教育,象徵了香港的中國歷史文化教育與內地的教育路向,從此有所不同,並且擁有自己的發展軌跡,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港英殖民時期港英政府先是抓住了教育的主導權,普及英語是那個年代教育的重中之重。畢竟,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港英政府要通過教育改變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獲取華人效忠,以便進行管理。然而香港是一個商業港口,不僅要與內地建立緊密的商業聯繫,同時還有大量人口不斷南下流入。如果想要改變所有人的母語,或者所有人都不會說中國話,一是難度太大,二是不利於經濟交往及發展。因此,港英政府需要政策調整,尤其是在「省港大罷工」的衝擊下,港英政權搖搖欲墜。
於是,「中國通」金文泰開始教育改革,在內地正如火似荼進行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進行批判時,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來區隔香港與內地。他帶領一批前清遺老,維護傳統儒家舊道德,強調社會尊卑秩序的復闢;避談國恥,壓制一切民族民主思想。可以說,他們教授的「傳統經典」無一不包,就是堅決不教白話文!魯迅曾大力批判英國殖民者以「中國國粹」以及舊文化中的奴性思想來麻醉中國人,達到管治目的。
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26年,香港人早已擺脫殖民身份當家做主,可香港的文化教育與社會心態仍然沒有與時俱進。香港既沒有對先輩們在這片土地上開疆闢土的完整論述,也沒有對滋潤我們幾千年中華文化文俗的有效傳承,更沒有對英國殖民的史跡從事去蕪存菁的檢討與論述。如果說,金文泰的改革措施,一舉促進了香港經濟發展,並深深影響和侵蝕了香港幾代人的思想。那麼今日香港,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我不由想起今年初《求是》雜誌,一篇題為《全面從嚴治黨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的文章,內容中提及在毛主席領導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思考「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這個問題,並有初步答案。毛主席認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唯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其後,有關探索仍然持續,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十八大指出了第二個答案,就是共產黨人須在接受人民監督的基礎上,進行自我革命,中國才能免於繼續經歷興衰循環的命運。
兩個答案前後相距六十多年,可見國家領導層一直非常重視並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黨和國家會將之視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我以為,這是一個認識並學習國家領導人重要思想的關鍵課題,同時對於思考香港未來出路和發展也將有着重大啟迪。
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使國家最高領導人始終保持清醒堅定的態度和未雨綢繆的眼光。他們為了篤行不殆,尚且提倡不忘初心、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並不斷反省和及時自我糾錯。那麼已風光走過180年的香港呢?雖然過往香港取得了不少成就與讚譽,但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無數障礙,我們是否也能夠時刻清醒自覺,又能否自我革命?或不斷自我革命?香港怎麼樣才能「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呢?

香港新闻社
有视界·有世界